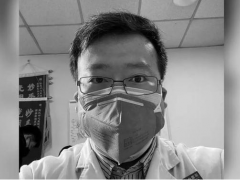沃伦·巴菲特在8月5日说,标准普尔对于美国政府信用的降级是错误的,如果由他来决定的话,他会给美国AAAA级,比美国降到AA+级以前的AAA级更高。不幸的是,巴菲特先生忘记了信用评级不仅反映债方还债的能力,也反映了债方还债的意愿。
巴菲特先生的立场有一定的逻辑,很多把美国信用当作大公司信用来看待的人也赞同他的观点。美国完全具有偿付债务的能力,因此,对于企业界的人,一个完全具有还债能力的公司在债务到期时不能还债是说不通的。当然,不能还债被称作“违约”,这对于一个公司、城市、州省、国家,都是有可能的。在信用评级中体现得并非是否违约。违约的可能性越低,信用评级越高。事实上,AAA级(甚至AA+级)都几乎没有违约的可能性。
这听起来简单,可真正复杂的是,尤其在非企业实体(比如美国)的情况中,“违约的可能性”包含两个明显有区别,但同等重要的因素:一是偿债能力,二是偿债意愿。在企业的情况中,还债的意愿是毋庸置疑的。具有还债能力却不还债的公司是非常不理性的,因为那会导致破产和企业解体。几乎没有企业的管理层会杀鸡取卵,也就是说,在具有资金的情况下不还债,会使公司走向破产。如果他们这样做,股东很可能会介入,采取更理性的管理手段。
最近,这个相同的逻辑被用来判断美国等国家的主权债务。很明显,美国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广阔的税收平台、顺从和有发言权的公民(即使美国人对此颇有怨言,但大多数美国人按时支付税收,而不像很多其他国家那样)——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华盛顿官员会采取一切必须的措施来获得财政收入或者大量削减支出以用于必需的国家经费。换句话说,人们认为,国家一直都有偿付债务的意愿和能力。
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已经动摇了美国按照能力偿债的意愿。各议员所陈述的——将在某些情况下允许国家债务“一小部分违约”,或者“选择性违约”的言论,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支持提高债务上限”的言论,传达了一个清楚的信息:在债务到期时还债的意愿并不如往常一样,获得两党支持。确实,当本应为两党共同追求的还债意愿,成为某一党的单面主张,而被另一党用来当做政治斗争的把柄要挟对方的时候,那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标准普尔在美国具有还债能力的情况下,认为美国没有还债的意愿。
类似的,在地方上也是如此。我们已经看到在某些地方,州政府遭到了文明的(和不那么文明的)反对和抵抗,因为他们试图通过要求减少政府公务员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来削减财政,大多数待遇较丰厚的私企雇员认为这已经降到了最低水平。所有这些——不论在政治倾向上你站在哪边——都暗示着政府也许没有采取必要的强硬措施来解决财政问题和避免长、短期债务违约的政治意愿。
这些事实暗示着,政府或许没有解决债务问题的意愿,不管是在地方还是在白宫。这是我认为导致标普采取行动的原因,并不是出于美国还债的潜在能力的考虑,只要两党一致决定要还债,这完全不是问题。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姆·弗雷德曼很多年前写过,赢得“胆小鬼”游戏(两车司机正面对开,看谁先由于害怕而突然转向)的方法是,在窗外挥舞方向盘(希望是你买的废品,不是你平时用的那一个),希望对面车的司机误认为你已经拆下了方向盘,无法刹车。换句话说,你要让对面的司机相信你已经疯了,最好马上转向,因为你不想转向,也不能转向。看着上个月的债务上限之争,很多观察家、包括评级机构,也许都已经得出结论,有时一方或两方都像在窗外挥舞方向盘的司机。信用降级反映了这样一个现实:也许在华盛顿,乃至在美国,负责任的“双手握着方向盘”的财政之车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