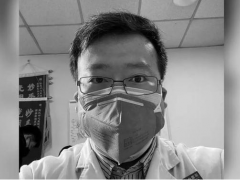跟她在小酒吧闲坐的时候,她向我抱怨,那些不牢靠的男人,全都风一样,从青萍之末而起,又归于无形,独独卷走了她大好的年华。我问她经历了多少男人,她数数自己的手指头,调皮地朝我笑,不记得了。
最短的一个星期,最长的一年多,她总是全力以赴,她把自己区别于那些热衷一夜情的人,她说她只是希望一个能有欢爱的男人,一个契合的男人,可是最后他们都一个个地靠近,又一个个地离开。
她喝口酒,忍不住叹息。为了向我证明这一点,她给我谈起那一段段的日子。飘雪的北京街头坐着男孩子单车后唱着歌回家,跟着一个人跑到阳朔,在漓江的竹筏上甜蜜地亲吻,以至于就在以前的深海二楼上,在喧闹的电子乐声中与人缠绵……
她说她感谢那些早已经消失了的男人,是他们让她逐渐地成长,是他们给了她许多欢乐和宠爱,日子越久,她就越是沉迷,她常常选择性地记忆,那些宛如红色粉墙上蒙蒙的阳光样的故事。她大笑——值了。那笑声现在都还回响在我耳边,她壮怀激烈的大笑的样子简直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我刚刚有点儿变通的时候,尴尬就降临了。
一次,跟一个同样在圈子的朋友谈起她,这个男人满脸的不屑:“你说,这和红灯区的人还有什么区别,只是不要钱而已,还以为得道?”这是个消费主义的时代,是她在消费那些男人,还是那些男人在消费她?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