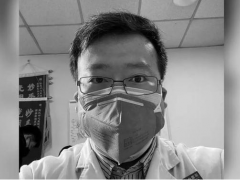1998年6月,中国政府通过国际竞标购得赞比亚谦比希铜矿85%的股权(赞方占15%干股) ,交由国家有色金属管理局直属企业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名:中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色建设)承建。同年9月,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公司(简称:铜陵有色)受中色建设之托,选派了以李周经、李冬青为负责人的15位工程管理和技术人员,参与矿山接收和长达三年的矿山恢复建设援建任务。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时光已经流转了近15个年头,如火如荼的印象和酸甜苦辣的感受变得依稀模糊,但记忆深处援建人员的名字却依然清晰:李周经、李冬青、陈贞民、盛忠义、王守林、胡国斌、王亚昆、叶向阳、王其芳、王训青、王庆华、何太龙、钱团平、王维刚,还有我,一共15人。
往事如烟,能挽回我记忆的群体印象只能是星星点点、斑驳陆离,但我亲自感受的往事却怎么也难以忘怀,历历在目。
1998年9月下旬,我们一行15人从五松山宾馆集合出发,经由合肥火车站到达北京南站。15人分三批出国,我和何太龙因签证问题被拖延下来(因我俩都有出国经历,可能是前后填的信息有差异,外交部在核实),何太龙几天后随中色建设的人出发了,留下我一个人度过了难捱的国庆。终于等到可以出国了,但只有我一个人去,中色建设非矿办事处的王淑珊交给我一沓机票和100美金,告诉我到了卢萨卡有人接机。有了在澳大利亚短期培训的经历,我并没有把这次旅行当回事。
对我们来说,现实威胁我们最可怕的疾病是疟疾。实际上当地的蚊子并不多,可怕的是它们带有疟原虫病体,虽然我们有蚊帐,但睡觉时不小心皮肤接触蚊帐,蚊子照样从蚊帐外叮人。在我们这批援建人员中,几乎每个人都得过疟疾。李冬青矿长第一个得了疟疾后无名发热了近10多天,我们轮流安排用凉毛巾帮他敷,后来发现是打针感染了。
我是第二个发病的。当天中午略感不适,我提前请假回来睡了一会。晚上李冬青矿长发现我高烧,坚持冒雨开车送我去60公里开外的基特伟市一个援赞的中国医生那里就诊,我断续烧了三天三夜,最后检查时尿样里含有血红蛋白,足见当时是多么严重。染病期间,国斌和同屋的人帮我送水送饭,铜陵有色的领导还特意叫食堂安排可口的饭菜。后来矿里传达,江苏外经建的一名工作人员因得脑疟身亡,这使得我们倍加小心。我当时想了土办法,多吃辣椒,实际上也不管用。
到了赞比亚后,短暂的兴奋和好奇之后就是思乡之情。特别是援建队伍中,大多数小孩还在上幼儿园或小学,工作之余,我们一群人会去踢足球,但夜晚来临时,生活还是相对枯燥一点。当时,只有李冬青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李矿长平时热心地帮我们收发电子邮件。另外,平时给家里写信,等对方收到了已经是两个周期以后的事了。收到家信是援建人员中最大的喜事。
初到谦比希,我被安排到3号房子里。那里并排有10多栋成套住房,因长久没有人居住,先到的同事着实清理了一阵子。当时一套房子约住6个人,李冬青矿长和我同住3号院,我和胡国斌住一间。我到达谦比西的当晚,李矿长向我介绍了谦比西矿的大致情况并布置我的工作,让我和设计院一道清理、编录接收的地质资料,同时负责矿山的环保工作,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每月要参加一次由原赞比亚铜业公司主持的环保月会。参加那样的月会,对我来说真是挑战,赞比亚的英语还是挺难懂的,越是那样的环境越是锻炼人,后来,英文版《谦比希矿恢复建设环境项目概要》还是我写的,我将写好的初稿送到环保局,环保局的官员很不错,帮我进行修改,为了感谢他,经请示李冬青矿长,我特意以矿里名义在附近中国餐馆请他吃了一顿中国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