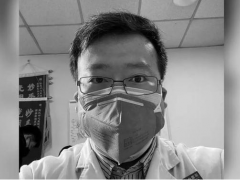编者按
作为“社会细胞”的中国家庭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宛如这几十年来在经济改革大潮中急遽变化的中国社会。最近,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在世界家庭峰会上表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调整使我国家庭的规模、结构、形式、功能等都发生明显变化,家庭发展面临一定挑战。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人口发展领域的巨大变革及经济发展,中国家庭呈现出五大变化: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核心化、家庭类型多样化、家庭关系松散化、家庭功能有所弱化。相对固定聚居的大家庭形态趋于解体,越来越多的新家庭形态出现,由此也带来了不同的新人群:独生子女、失独父母、丁克族、单亲母亲、单亲子女、不婚族。这些新家庭形态也出现不同于以往的各种新观念,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价值观冲突明显,家庭代际呈现新的对话、磨合。
在当今中国,社会流动性大造成一方面家庭成员的自由度变大,另一方面家庭关系松动、缺失,家庭这个社会细胞的稳定性令人担忧。无数从农村流动向城市的人,无数行走在国内海外之间的人,造就这些词汇:漂一代、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空巢老人等等。即使在表面上仍然保持稳固形态的家庭内部,互联网对家庭成员交流模式的冲击也无处不在,家庭财富增加带来的经济理性更在悄然取代传统的家庭价值。
流动的时代,网络的时代,财富的时代,这些都是与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中国格格不入的事实,而它们已经到来且不断加速前进,摇晃着、“拆迁”着建立在传统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家庭大厦,使之渐渐面目全非。被裹挟着前进的我们,是否还能认识家庭的含义,把握家庭的命运,重建家庭的价值?
毕竟,我们都是家的儿女,无论如何我们的内心都需要珍藏一份对家庭温暖的认同与向往,这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稳定所系。或许,我们需要回到家庭故事中那些熟悉的场景,咀嚼那些早已司空见惯的变化,从中去寻找、把握中国家庭的未来。
流动时代,亲情在流失
家“漂”在中国大地上
随着“80后”一代逐渐进入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而立之年,他们的父母开始加入“漂一族”行列。本该安享晚年,却为帮儿分忧,照顾孙辈,不远千里“漂”至陌生大城市,为儿养儿。语言不通、文化差异、情感孤独,最痛心是儿女的不理解,每天念叨“恨不得立刻离开”。“老漂族”的日益庞大成为大城市里的一道风景。
清晨6点多天蒙蒙亮,在安徽省合肥市南郡明珠小区内,59岁的肖金枝在给儿子媳妇做早餐,然后叫醒5岁的小孙女,帮助穿衣喂饭后,坐20分钟的公交车送去幼儿园,这便是她一天洗衣打扫、带孩子的异乡生活的开始。
为了照顾孙女,肖阿姨和老伴从安庆潜山县来到合肥市已有5年,对于家乡的思念却越来越浓,“看见路上有人说安庆话,就想凑上去聊两句,经常会梦见家乡的人和事。但儿子儿媳工作忙,我们走不开啊”。
许多老一代打工者仍在坚持。58岁的熊邦明来自重庆北碚区东阳镇,给重庆一家花木公司打工已经有10年时间,老伴也和他一起住在这里。他指着住着的简易板房对记者说,这是公司花3万多元在桥洞里给工人建的。每户一个屋子,他的屋子紧靠着洞口,可以看到外面的江边。
家里的大米、蔬菜堆在床侧,灰白的水泥墙、昏黄的灯光,除了床边挂着的几件衣服,屋里没有鲜艳的颜色。
熊邦明已经连续3年没有回家过年了,他有一个25岁的儿子,在广东当厨师。他说,老家有4间房子,还有1亩多地,现在都给兄弟们照看了。城里的生活累一点,但还是挺好的。晚上5点半下班,吃完饭就去散散步。
熊邦明说,自己还没有想过回家,现在干活挣钱,等老了干不动了再回家种田。记者问他还打算干几年,他沉默了一会儿说:“10年。”
留守空巢与追逐自由
12岁的王冰,在河南省驻马店市平舆县一所寄宿制学校读书。自从去年4月份匆匆见过爸爸一眼后,王冰已经快一年没有见到父母了。王冰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在山东打工,家里只有他和奶奶。平舆县是劳动力输出大县,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导致留守儿童数量激增。
去年4月份,奶奶突然发病倒在地上,把12岁的王冰吓得大哭,幸亏周围邻居帮忙,才将奶奶送到县城医院抢救治疗。第二天,王冰抱着急忙从山东赶回来的爸爸大哭了很久,央求爸爸不要再出去打工了。“我不想让爸爸再出去了,我害怕奶奶再病了。”王冰说,“我也想像家在县城的同学一样,放学就能回家和爸爸妈妈奶奶一起吃饭。”
除了农村留守者外,城市留守者也不鲜见。“现在不是常说‘剩男剩女’吗?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都是‘剩爸剩妈’了。”刚刚从浙江某政府机关退休的刘丽娅告诉半月谈记者,自从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老两口就被“剩”下了。
“孩子不在家,老公工作常常外出,很多时候就我一个人在家里发呆,不知道该干什么。”刘丽娅告诉记者,为了关注孩子的一举一动,她开始聊QQ,甚至患上了网络依赖症。
而子女们似乎对此有不同见解。刚从山东青岛转职到浙江杭州生活的刘嘉宾坦言,自己一个人过,还挺自由的。“在青岛的时候跟父母一起住,父亲是单位领导,总拿他的那一套训人,经常发生意见冲突。现在偶尔打电话回家,父亲倒反而会认真听我在说什么了。我觉得这样的距离感挺好。”
对传统家庭说“不”的年轻人
在城市,新家庭形态越来越多,同时也正从开始的“异类”变成普通人可以直面、理解的范畴。在很多“80后”“90后”眼中,夫妻或者家庭可以直接被朋友、工作所取代,当下的年轻人更注重个人的体验和感受。“现代人受传统家庭观念的束缚已经越来越少了。”
32岁的赵晗(化名)是一名“不婚族”。“父母总是认为要传宗接代,但如今离婚率高企,结婚并不代表就能幸福,真正的幸福还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多年来,对于父母的各种“相亲”“逼婚”,甚至要“断绝父子关系”,赵晗无不一一将其拒绝,“现在父母开始尊重我的选择”。
现代社会中,个人是家族的延续的概念正在淡化。已经35岁的辛洁和老公已经结婚9年了,但两人至今还没要孩子,反倒养了两只猫一条狗,小日子过得十分惬意。辛洁说:“我们是决定好了要做丁克的,家里人开始也反对,但这终究还是我们的事情,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可能是我们两个都不太喜欢小孩子吧。其实这大概就是所谓价值观的差别,不过我觉得这并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关键还在于自己愿意过什么样的生活。”
失独父母的新家庭
68岁的熊淑萍起了个大早,匆匆赶去社区的会所。熊淑萍是星缘联谊会的会长,每周二是固定的文艺活动日。“星缘联谊会”是重庆市沙坪坝区为关怀“失独父母”群体,而专门组织成立的一个民间团体,引导“失独父母”走出失去子女的悲痛,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
7点刚过,几位擅长厨艺的会员就开始忙活起来。9点刚过,会员们陆续来到会所,还特意穿上了专门的演出服装,开始载歌载舞。会员们脸上都挂着笑,彼此之间熟稔地打招呼、开玩笑,没人看得出来他们都是失去独生孩子的父母。然而,他们的内心,也只有相互倾诉时才能获得一丝丝的慰藉。
熊淑萍也是一名失独母亲。13年前,年仅28岁的儿子因为发生意外离开人世,只剩下她和身患肾病的老伴相依为命。整整10年,熊淑萍常常梦见儿子,无法从丧子的悲痛中走出来,也拒绝和外人交流。“在星缘会,我们都是有同样经历的人,相信自己的孩子去世后变成天上的星星看着我们,我们得为了孩子好好活下去。”她说。
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很多“失独父母”曾经只能默默地独自舔舐自己内心的伤口。重庆星缘联谊会、武汉连心家园联谊会和上海星星港的“抱团取暖”模式逐渐获得越来越多“失独父母”的认可。
熊淑萍说,联谊会定期有活动和聚会,大家都是同样的失独父母,伤心的事可以说,开心的事更可以说。尤其是逢年过节,大家聚在一起,唱歌跳舞,而不是独自在家对着孩子的照片流泪,这样才能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和热情。“日子总要过下去,孩子不在了,我们更要替孩子好好活着。”她说。(记者 张莺 张紫赟 刘巍巍 张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