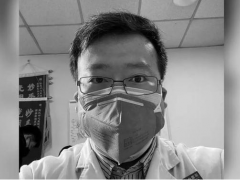生活在接合部的“居民”们
一些城乡接合部的原住民享受到了发展带来的红利;一些外来者涌入这里,辛勤奋斗寻求发展和尊重;但也有一些因土地征用补偿而“一拆致富”的农民,在拥有财富之后,却不知所措,反而迷失了自我。《瞭望》新闻周刊走进了这些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居民”。
本地人:分享城镇化发展红利
一些村镇及时抓住城镇化机会,创新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让村民过上了比市民还富裕舒心的日子。
居住在石家庄市槐底社区的7600多名居民,已全部从过去的农业户口转成了城镇户籍。社区党支部书记陈玉信说,村里吸引投资,建起了一大批涵盖餐饮、零售、住宿、建材、教育、金融等领域的三产项目,固定资产达300多亿元。如今,家家户户都住上了300多平方米的高层住宅,每月还提供免费的粮、油等副食,人均年收入超过2.5万元。
但也必须看到,土地利用秩序混乱、治安环境差、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缺位、“人口倒挂”严重等顽疾的存在,仍是目前大多数城乡接合部的真实写照。
本刊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城镇化后,一些农民虽不再种田,但其思维方式、教育水平、消费观念、生活方式等,仍停留在“农业社会”时代。
外来者:努力奋斗寻求尊重
除了原住民,居住在城乡接合部的主要有三类人群:外来打工人员、城市低收入者以及农村人口。他们多为弱势群体,文化水平不高、掌握的技能不多,通常从事建筑、快递、环卫、家政等体力劳动,多为个体经济,较少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工作报酬偏低。
此外,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年轻人,也选择生活成本低、交通便利的城乡接合部作为圆大城市梦的垫脚石。
来自安徽阜阳的郑春来在上海九亭镇居住了6年,夫妻俩租了一间十几个平方米的小房间,除了床和简单的桌椅外,杂物几乎堆满整个房间。郑春来告诉本刊记者,妻子在附近的工厂上班,他每天早晨在路边卖豆浆和煎饼,两人一年收入不足5万元,但比在老家种田赚得多。
“有住、有吃、有钱赚,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已经不错了”,郑春来说,“我们不怕受苦受累。只要能多赚些钱,让老人过得好一些,让两个孩子上得起学,就心满意足了。”
对于他们来说,吃苦不怕,怕的是得不到尊重。来自江苏省睢宁县的姚健在上海打工,遇到困难时基本不找政府,因为他担心政府对上海本地人的态度和对外地人不一样。“我也靠劳动生存,我也纳税,我们外来打工者应得到更多尊重。”
异化者:“一拆致富”的迷失
大规模的土地征用造就了一大批“土豪”,数套还建房和高额补偿金,使拿到土地赔偿的村民身家倍增。本刊记者采访发现,一些“一拆致富”的农民,迷失于瞬间的资产膨胀,扔了工作、大肆挥霍继而再度返贫,有的甚至因“黄赌毒”而成为“阶下囚”。
武汉市东西湖区额头湾村过去是城市边缘的一个农业村,村民靠种地和养鱼为生,超过八成的家庭基本无存款。2010年,拆迁让村里发生了巨变,每户除了还建房,还能得到50万元拆迁款。
村党支部书记陈军说,突如其来的“巨资”让村民心态发生了变化,四五十岁的人大多吃过苦,不少还能保持本色;但年轻人往往大肆挥霍,有的嫌工资低辞职不干了,有的天天呼朋唤友、吃喝玩乐。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今年2月,武汉警方在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左岭街黄陂岭村端掉了一个专业赌博团伙,不少赌客是周边村里的拆迁户。居民詹先生说,该地区被纳入政府的拆迁规划后就赌风日盛。“牌打得很大,一般半天就能输赢两三千元。家破人亡的例子不少。赌红了眼,一天输上百万,没钱了就借高利贷,利息每天千分之五,怎么还得起?”
这样的拆迁户,往往被贴上“土财主”、“暴发户”的标签。但在暴富之前,他们已是一个矛盾体:生活在城乡接合部,游走于城市的边缘,没有城市人优良的条件,但比起地道的农村人又有些优越感;没有城里人的秩序,又缺少农村人的朴实。
拆迁户“不劳而获”的巨额资产,还让一些周边居民“红了眼”。广州市萝岗区中新知识城辖区内的农民,得到了巨额赔偿款,变成了“市民”,但与知识城一线之隔的农民却依旧贫穷,引发了不公平感。城乡接合部内部,正在逐渐呈现出新的二元分割。□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茁卉李芮詹奕嘉白丽萍陈俊魏宗凯孔祥鑫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