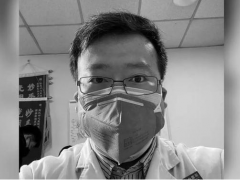●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打击非法集资活动,其实是用间接融资的手段处理了直接融资问题,不能为民间金融的合法化预留空间,不能为集资监管从一味的“堵”转型为有步骤的“疏”提供法律基础。
●在刑法规制上,对非法集资活动的刑罚,应当以“擅自公开发行证券罪”代替“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对非法集资活动进行刑法规制的讨论,虽然只涉及《刑法》上一两个罪名的调整,却事关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对于非法集资活动,我国《刑法》中适用最为广泛的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以此定罪既不符合对该罪的法律解释逻辑,错误扩大了其适用范围,也不利于构建对非法集资活动的有效规制体系,并且没有为民间金融的合法化预留空间。
对合理需求的非法集资活动,应以疏导代替堵塞,以直接融资手段进行处理。体现在刑法规制上,对非法集资活动的刑罚,应当以“擅自公开发行证券罪”代替“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规制非法集资活动效果并不好
非法集资活动在中国现实生活中频繁发生、层出不穷,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种类型是集资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巧立各种名目诈骗社会公众资金。对这种欺诈行为,毫无疑问应当予以禁止,我国《刑法》上相应规定有“集资诈骗罪”。
但我们要讨论的是另一种类型的非法集资活动。这种类型的集资者往往有合理的集资需求,但是由于不能从正规融资渠道获得资金,或者试图规避正规渠道带来的较高融资成本,而通过正规融资渠道之外的其他手段获得资金。
我国从原有的集中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正规融资渠道较多偏向国有企业,忽略民营经济的融资需要。这是我国非法集资活动频繁发生的制度环境。
出于对社会公众利益保护的考虑,各国都会对非法集资活动进行一定程度的规制。其中我国目前的规制手段最为严厉。对大量没有直接采取公开发行股票或公司、企业债券形式的非典型性非法集资活动,实践中多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从实践来看,此种刑法规制的效果也很难令人满意。自从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将该罪名引入刑法以来,非法集资活动在现实中并未得到有效抑制。反思现行针对非法集资的刑法规制手段,已经很有必要。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打击非法集资活动,存在法律逻辑的错误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理各类非典型性非法集资活动,并不符合非法吸收存款罪本身的法律解释逻辑。
目前大家基本承认,本罪来自《商业银行法》的相关规定,是违反《商业银行法》相关规定的刑事责任。从立法目的角度观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立法目的在于维护商业银行必须经过特许才可设立的市场准入制度,因此,所谓“吸收公众存款”的概念必须放在从事了商业银行本质业务的层面才可得到正确解释。按此解释逻辑,则现实生活中大量的非典型性非法集资活动并不能被界定为非法从事了吸收公众存款的业务。
法律所以对商业银行规定严格的监管制度,是因为商业银行特殊的资产负债结构,导致商业银行极端脆弱。法律在承认这一特殊资产负债结构下,为商业银行提供特殊保护———即所谓的存款保险制度,以维持存款人的信心。因此,国家不得不对商业银行的市场准入和持续经营过程都加以严格控制,防止商业银行滥用存款保险制度的保护,由此形成了现有的商业银行特殊监管制度。
在这一思路下,作为商业银行本质业务的吸收公众存款业务,并非是指一般存款,而只能是活期存款。将“吸收公众存款”中的存款解释为活期存款,意味界定存款的关键因素是存款人债权的期限。
此外,《商业银行法》第11条第2款界定的是商业银行本质业务,因此不应包括那些因为急需偶一为之的民间借贷行为,不论其借款期限是否固定。换句话说,必须是长期“从事了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才会被视为实质上经营了商业银行业务,偶尔向多人借了不定期限的借款,并不能就构成非法从事吸收公众存款业务。
从我国实践来看,应当将那些长期或者多次以非固定期限的还本付息方式吸收资金的行为界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对于实践中偶然发生的此类借贷行为,则应当视为合法的民间借贷活动,不予干涉。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打击非法集资活动,是用间接融资的手段规制直接融资问题
其实,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打击非法集资活动,本身就是错误的,不利于构建合理有效规制非法集资活动的法律框架。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打击非法集资活动,其实是用间接融资的手段处理了直接融资问题,不能为民间金融的合法化预留空间,不能为集资监管从一味的“堵”转型为有步骤的“疏”提供法律基础。
集资可以采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不同模式。对这两种不同的融资模式,法律相应发展出了两套不同的集资监管制度。
对直接融资,法律一般通过证券法予以调整。证券法的核心在于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要求资金需求者通过注册,披露广泛信息,以让资金供给者自己做出是否提供资金的投资判断。
对间接融资,法律则设置了与证券法完全不同的监管思路。此类法律强调对金融中介机构的安全性和健康性要进行持续监管,以保证金融中介机构能够审慎经营。最为典型的就是《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严格限制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要求保证一定的资本充足率或者净资产比例。此外,还通过严格的市场准入和特殊的市场退出措施,减少金融中介机构破产的可能以及破产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我国处理非法集资活动的现有实践,由于将多数非法集资行为都归结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实际上是混淆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以间接融资的方式统领了所有非法集资行为。而多数民间非法集资往往是集资者自己使用资金,更类似于直接融资模式。
将所有非法集资活动都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当然具有容易理解也容易操作的优点,但也可能带来简单粗暴的后果。
一是在性质认定上的困难。从合约性质上讲,存款一定意味着还本付息,因此,在各类界定吸收公众存款的相关文件中,都明确规定“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为其主要特征。但实际上,非法集资的手段多种多样,承诺还本付息只是吸引投资者的一种方式,分享未来收益但不约定固定回报,也是可能的选择。如果一味以固定回报承诺作为界定非法集资的基本标准,对非法集资活动的界定就可能范围过窄。
二是,一味禁止非法集资绝非立法本意。基于种种原因,我国目前合法集资途径有限,大量合理的资金需求无法通过合法集资途径满足,才不得不走上了非法集资的道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金融体制的改革,开放更多合法融资渠道、将民间融资合法化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
在直接融资法律制度中,国家不对集资者获得资金之后的使用进行持续监管,法律通过建立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要求集资者在事前和事中都通过信息披露向投资者提供充分信息,使得投资者可以自己做出投资判断。为了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法律规定了一套严格的反欺诈制度和相应便利的诉讼程序。这套制度有利于促进投资者的成熟,也有利于形成一个快速反映相关信息的资本市场。
因此,放弃用间接融资手段处理非法集资问题,改用直接融资方式,不仅是为了更好实现保护投资者的公共政策目标,也是我国经济转型所选择的方向。
设立“擅自公开发行证券罪”取代“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因此,《刑法》上可以用来规制非法集资活动的直接融资手段,只有第179条的“擅自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罪”,因此应当扩大该条的适用范围。
无论非法集资活动如何形式隐蔽、手段翻新,其实都不过是某种投资安排。投资者投入资金到某个共同事业中去,其目的不过在于依赖他人的努力,获得利润回报,尽管这种回报可能表现为固定收益的承诺(债权型)、收益分享(股权型)或者其他安排。这种投资安排无论表现为何种形式,都可被界定为证券,只要集资者未经批准,向社会公众以投资安排的形式募集资金,都可以构成本罪。
因此,为了保证更好适用本罪打击非法集资活动,本罪应当改名为“擅自公开发行证券罪”,包括所有未经批准,擅自公开发行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的行为。
同时,《证券法》也应当相应扩大证券的定义,以扩大本罪的适用范围,不再仅仅局限于股票或公司、企业债券。对证券的狭窄定义限制了市场的证券品种和市场层次,也限制了交易的多样性和相关性。更重要的问题是,限制了《证券法》和《刑法》的适用范围,不利于对投资者的保护。
改革这个罪名事关金融制度改革和民营企业的发展
对于存在合理需求的非法集资活动一味禁止,并非立法本意。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打击所有非法集资活动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资金是企业的血液,合理有效的融资制度是为企业增长输血的血管。在经济已经飞速发展、金融仍在缓慢转型的中国,构建一个合理有效处理非法集资活动的法律框架,是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刑法手段是这个法律框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也是可能导致无数民营企业家身陷囹圄的关键。对非法集资活动进行刑法规制的讨论,虽然只涉及《刑法》上一两个罪名的调整,却事关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彭冰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