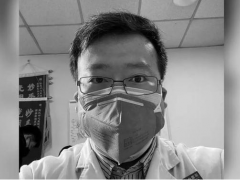访谈嘉宾:刘仁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刑法室主任
日前,复旦大学177名学生给上海高院写“求情信”,为“复旦投毒案”犯罪嫌疑人林森浩求情“免死”一事,引发热议。“求情信”是否发挥作用,该如何看待“求情信”,以及围观者的心态?
“求情信”更像“法庭之友”
1、新京报:目前的舆论两极分化比较明显,支持者认为,复旦学子有权表达对“死立决”的态度。质疑者认为,复旦学子的同情心用错了地方。你怎么看?
刘仁文:从言论自由的角度看,对同一个公共事件持不同观点,是完全正常的。
即便在美国,尽管死刑只是作为一种极其例外的象征性刑罚而存在,但如果要判处或执行一个人的死刑,“反对死刑”和“支持死刑”的声音都会通过各种渠道发出来。
但是,在“复旦投毒案”判决时,社会上似乎只有支持死刑的声音,而没有反对死刑的声音。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能出现这样“救人一命”的声音,总的来说还是件好事。
值得深思的是,我国的“死刑”有很强的文化基因。比如,尽管“求情信”出来之后引发了不同的争议,但对复旦师生进行指责的声音还是占很大比例的。同时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仅仅把“求情信”寄给法院这样一种正常的民意表达,就会受到如此大的反对?
2、新京报:签署“求情信”的师生,是否如某些人所指责的“法盲”?
刘仁文:首先,不管是谁,都有表达诉求的权利,这和自身是否具备法律素养没有太大关系。其次,即便是“法盲”,也不宜指责。法院应当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听取民意,只要不是被民意裹挟。
3、新京报:国外法院如何去倾听民意呢?
刘仁文:国外有一个“法庭之友”(或译作“法院之友”)制度。简单说,“法庭之友”不是诉讼当事人的任何一方,可以是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回应诉讼双方的当事人请求,或是出于自愿,提出相关资讯与法律解释的法律文书给法庭,以协助诉讼进行,或让法官更了解争议的所在。提出这种法律文书的人,被称为“法庭之友”。而复旦师生的“求情信”,有点像是国外的“法庭之友”。
4、新京报:有人认为,“署名者不及师生1%”,民意诉求和联名人数有关系吗?
刘仁文:社会关注的重点,还是应该放在“求情信”本身是不是在摆事实,讲道理,有没有证据支持,而不是关注求情的人数占多大的比例。
人数多少可以反映出部分问题,但不能作为主要指标来衡量问题。
“量刑判断”需要回归法律
5、新京报: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求情信”是在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之后发起的。发起人之一复旦大学教授谢百三也表示“对嫌疑人林森浩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话,觉得有些不妥”,“当庭宣判”的问题怎么看?
刘仁文:我国目前强调当庭宣判,目的是防止事后暗箱操作,出现司法腐败等现象,但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应当辩证地看。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作《美国司法细节观察——与一位美国法官的通信》,专门提到这个问题。在美国有一个缓刑部门,相当于量刑建议部门,是法院的得力助手,从他们那里,可以了解到被告人的罪行及其生活状况,如他的家庭、教育、工作,以及他的医学或精神上的问题,还包括他的犯罪史。
按照我国法律,如果二审宣判死刑,最高院核准死刑后,七天就要执行死刑。我觉得这种制度设计不恰当,杀人还是不急为好。像这样的案子,在开完庭后,确实要了解当事人的人格、背景如何,这样才比较科学,防止简单的“杀人偿命”。
6、新京报:学生们提出这个诉求是否合理合法?如果有诉求,该如何表达?
刘仁文:我认为这个诉求合理合法。因为他们没有去干预司法,只是把信寄给了二审法院,请他们考虑,便于法庭进一步了解情况,了解当事人的背景。
法官该不该收这些信、该不该纳入量刑考虑的范畴?目前没有明确规定。为了更好地吸纳民意,我们应该有类似“法庭之友”的制度。例如像这样的请求信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门槛,由法院内部什么机构进行接收和转发,承办法官应否入卷等等,都应当规范化。
7、新京报:他们的诉求是否会有效?
刘仁文:至于他们的诉求是否有效,我觉得“求情信”只能供法官参考。实际上法官应该不受舆论干扰,但是在中国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求助媒体,法官会有一定的压力,我非常担心一些领导看了以后给法院一些批示。
法官如果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平心静气地看看这些求情信,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妥,反而有利于他全面思考问题。就怕在中国目前的司法体制下,法官的地位不是很高,如果受到外界的压力,不管最后的结果正义不正义,都不是法治健康运作的结果。
8、新京报:根据报道来看,是律师建议复旦学生写求情信,让林的家人、同学和被害人黄洋的父亲沟通,尽最大努力求得他的谅解。律师此举是否涉嫌干预司法?
刘仁文:我基本的意思是,如果律师只是给出建议,没有问题,因为写求情信的同学和老师还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写信的,没有被谁要挟、诱惑或欺骗。当然,如果律师直接或间接采取了要挟、诱惑或欺骗的手段,那肯定是违反职业道德的。
死刑之争亟须“超越悲剧”
9、新京报:这个事件的本质,其实是民意与死刑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处理,你怎么看?
刘仁文:这个问题特别复杂,民意是一把双刃剑。有时我们看到,民意在死刑上是推波助澜的。从刘涌案到药家鑫案,再到李昌奎案,当事人都是因为民意而死。还有郑州张金柱案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他说自己是被媒体判了死刑。
但也应看到,民意也救了一些人,例如吴英集资诈骗案,本来二审被判处了死刑,后来民意反应强烈,最高法院最终没有核准死刑。
在任何一个国家,民意对司法判决都不可能没有一点影响,但是里面确实有一个度的问题,在我国,相关规范不够成熟,民意对死刑的影响更大。
最理想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民意通过一些正常渠道表达出来,法官给予考虑,至于判不判死刑,法官独立思考。但现在我们达不到,像吴英因为民意活下来的毕竟是少数。
现在法官最怕的可能不是民意本身,而是民意通过舆论等被上级领导关注了以后,领导采取批示的方式,批给有关领导或上级,给承办案件的法院和法官造成很大的压力。为了仕途或前途,法官不可能不听上级或领导的意见。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就是上级领导和部门绝不要批示案件。
10、新京报:如果说从法律上平衡民意与死刑的关系稍微容易一点的话,那么从根本上清除“死刑”的文化基因,可能就没那么简单了,而这却是民意的一个重要基础,该怎么办?
刘仁文:所以我一直呼吁要“超越悲剧”。我印象很深的一个例子,2000年的时候,南京市发生一起凶杀案,四个苏北的无业青年杀了一个德国人普方一家四口。听说这四个孩子根据中国法律将很可能被判处死刑,普方的母亲在跟亲友商量之后,写信给中国法官,说不希望判处这四个青年死刑,“德国没有死刑,我们觉得,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
当年11月,由普方夫妇的同乡和朋友发起,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国人设立了以普方名字命名的基金,用于改变苏北贫困地区儿童上不起学的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庭审中的一个细节给他们触动很深:那四个来自苏北农村的被告人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没有正式的工作,“如果他们有个比较好的教育背景,就会有自己的未来和机会。”
目前世界上废除死刑的现实和趋势,是不是可以做一些适当的介绍和引导?绝大多数人生活在习惯中,我们的思维会受到周围人的影响,如果周围很多人都还简单认为“杀人偿命”,那大幅度减少死刑直至最后废除死刑的目标就永远无法实现。
当然,我们也不是倡导无原则的宽容,罪行必须得到严惩。在西方很多国家无期徒刑就被认为很重了,但在我国认为死缓还便宜他了。
如果像纪念普方那样,就如复旦有同学说的,他们想捐款以受害人的名字来命名一个基金会,我认为这样的方式将可以慢慢改变“杀人偿命”的文化基因。(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实习生 孟亚旭)